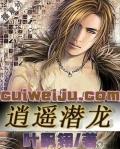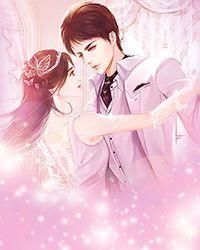沸腾文学>大召荣耀笔趣阁 > 第987章 放生三郡(第2页)
第987章 放生三郡(第2页)
又是一整日的滂沱大雨,入夜才停。
都督府后堂,檐角还滴着水,堂内一盏孤灯,灯焰被窗缝透进的潮气压得摇摇欲坠。
灯光下,两份急报摊在案上:其一,北境三处隘口,五日之内又涌出流民近两万之众,冀东润丰郡陶关之外,立起了「冀州屯田都尉」大纛,大肆收拢兖州百姓,白昼牧马,夜举篝火,鼓角相闻。
其二,郑天锡于五月十五日夜下令,因兖州与徐州不曾遵守约定的半月之期,没有再往玉滨湾参加盟台,故自当日起,青州境内凡无「路引」之商队粮船,一律扣留,算是断了兖州与徐州盐粮换购的渠道,也将三州彻底割裂。
师恩行坐在案前,盯着两份急报久不言语,孟不离立在一旁,面色凝重:“这几日各隘口流民愈发汹涌,昨日一天便过四千,照此下去,不出一月,泰山、东平两郡青壮就要走空了。”
师恩行仍旧不语,孟不离迟疑片刻,忍不住问道,“都督,属下不明白,您在兖州经营多年,仁义之名广播四海,深受百姓爱戴,可也就是这些百姓,为何仅凭一纸文书,就能如此毫不犹豫的离开,这……”
“趋利避害而已。”师恩行微微一笑,打断道,“快二十年了,主少国疑,二王残暴不仁,三州百姓深受荼毒,尤其是我兖州,尽管现在已不受他管,但惧怕早已深埋骨髓,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,若没有实在无法割舍的东西,自然会选择离开。”
孟不离一脸愤然:“当真是毫无情义!”
“并非不留情,而是他们不敢再做梦了。”师恩行将那两封急报慢慢折起,折成四四方方的一块,就像给亡人叠的纸银,灯火晃在他指节上,映出一片青白,毫无血色。
“不离,你说我这些年广施仁义,是为了什么?”他的声音极轻,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孟不离沉默片刻,试着回应:“为……为了让兖州少死人,也为让百姓记得都督的恩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师恩行微微一笑,不置可否,他把那纸块放到灯火上面,火舌舔上去,转瞬焦黑,随即又有火星一跳,映得他眼底像两口枯井,井底却燃着幽暗的光。
“兖州于我,于百姓而言,是家,也是囚笼。”他把燃烧的纸扔在地上,盯着它逐渐变为灰烬,“项瞻在陶关外牧马举火,不是给我看的,是给兖州百姓看的……他在告诉他们:跨出一步就能活,可留在原地,就算不死,也与囚犯无二,生路与死路之间,我让他们选哪条,才算仁义?”
孟不离眼底微红,半晌才挤出一句:“可再这么放人,兖州就空了,眼下郑天锡又断了商路,仅凭我三郡之地,怕是撑不到麦收。”
“空得了田地,空不了山河。”师恩行抬起头,脸上竟带着一点极淡的笑意,“郑天锡太倔了,对截他商船的罪魁祸首无能为力,就只能把气撒到袁季青身上,我不过是受了无妄之灾罢了。
他又回到桌案前坐下,在案上缓缓摊开一张素绢,提笔蘸墨,沉吟片刻,写下两行字:
「愿以三郡之地,换我治下万民一梦。
梦醒之后,此地无我,亦无兵戈。」
“都督!”孟不离死死盯着这两行字,声音发颤,“您,您要弃兖州?”
“不是弃,而是放生。”师恩行从怀里掏出一枚锦盒打开,将里面的都督印绶取出,放在那素绢之上,“我这便写下降表,不奉朝廷,不拜盟台,直呈项瞻,印、地、兵册、户籍,尽付与他。”
喜欢大召荣耀请大家收藏:()大召荣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