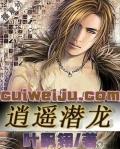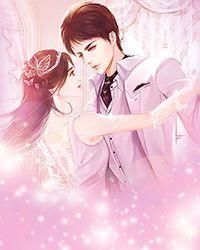沸腾文学>虎贲郎中 > 第696章 稷山盗现(第1页)
第696章 稷山盗现(第1页)
稷山东麓,半坡柏林中。
韩高三十余人隐匿其中,他们都是往昔稷山盗的经典打扮。
就连皮铠上的印花,都是与当年一样,是同一套模具压制而成的纹理。
不同于周围面具遮脸的稷山盗,韩高只是用半。。。
夜阑人静,祁连山下的归藏庐前,一盏孤灯摇曳如豆。风从戈壁吹来,卷起黄沙,掠过屋檐下悬挂的铜铃,发出低沉而悠远的回响。那铃声不似人间所有,倒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与嘱托。
吕哲已不在庐中。
但炉火未熄,案上竹简齐整,笔洗清冽,砚台边还留着半干的墨痕。仿佛他只是出门散步,片刻便会归来。可那封写给天下的绝笔信静静躺在木案中央,字字如钉,将他的离去钉入历史的骨缝之中。
游方僧人带着信西去敦煌时,并不知自己背负的是一个时代的句点。他翻越乌鞘岭,在风雪中跋涉七日,终于抵达莫高窟。蔡琰亲迎于洞外,披素衣、执松炬,身后站着义学三十六长老。她接过信,双手微颤,却一字一句读得清晰。读罢,全场默然良久,唯有洞顶滴水之声,敲打着石壁上的飞天壁画。
“先生走了。”蔡琰轻声道,“可永昌没走。”
她命人将信刻于第17窟入口左侧石壁,又另立碑记:“此地为启蒙之所,凡愿学者,无论男女贫富,皆可入内听讲。”自那日起,义学昼夜不息,烛火通明。孩童习算术,妇人读律令,老兵学医理,匠人研水利。纸张不够用,便以沙盘代纸;无师可授,便互为师生。知识不再是权贵的私藏,而是田埂上行走的阳光。
三年后,第一代“民议子弟”走出义学,奔赴十三州任职。他们不穿锦袍,不乘高车,只携一卷《宪章》、一本账册、一副药箱或一把铁尺。他们在乡间设立“公议亭”,每逢初七集会,百姓围坐一圈,争论赋税多少、渠口如何分配、学堂该建何处。争吵激烈时,有人拍案而起,也有人掩面哭泣,但从无人拔剑相向??因为他们记得吕哲说过:“争而不破,才是文明。”
而在洛阳,新的制度正经受风雨考验。
《重光决议》虽已颁行天下,但旧势力并未真正退场。士族暗中串联,称“妇人参政伤风败俗”,阻挠女议堂在南方诸郡设分会;豪商勾结地方官吏,借“德能绩三考”之名塞私亲、压寒门;更有甚者,冀州刺史竟伪造灾情,骗取公仓粮米三千石,转手售予胡商牟利。
消息传至太学,新任申冤司主簿郑覃怒不可遏,连夜提笔上奏:“今有官如虎,噬民膏血;法令如纸,难束权臣。若不清查,则民议不过虚名!”奏章呈上,献帝年仅十七,却已颇具主见。他召集群臣于宣政殿,当众宣读奏文,然后问:“谁愿往冀州查案?”
满朝文武低头避视,唯有一女子出列。身着青布深衣,发挽素簪,正是蔡琰。
“臣愿往。”她说得平静,“非因胆大,实因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再度陷入沉默。”
于是蔡琰挂“钦差监察使”印,带两名书吏、一名老兵护卫南下。沿途所见,令人心寒:村庄荒芜,田地抛荒,老弱倚门而望,不见炊烟升起。到了冀州治所信都,府衙门前竟立着一座金漆牌坊,题曰“惠政流芳”,而旁边沟渠里漂浮着饿殍。
她不动声色,先访乡老,再查账册,三日之内便理清脉络:原来刺史联合豪族,假借修渠之名强征劳役,又谎报旱灾骗粮,实则囤积居奇,待价而沽。更令人发指的是,他们还将不愿服徭役的农户贬为“贱籍”,禁止其子女入学、婚配良家。
蔡琰当场下令查封府库,拘押主官,并启用《申冤司条例》第四条:“凡重大贪渎案,须由五县以上民众代表组成陪审团共审。”于是周边各县推举农夫、织妇、教习、医师共三十七人齐聚信都,在太守衙门前公开听证。
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。
百姓第一次坐在高堂之上,手持木牌表决“有罪”或“无罪”。被告刺史起初冷笑:“尔等泥腿子懂什么律法?”直至一位白发老妪站起,颤抖着掏出一张泛黄的田契,说:“这是我祖父传下的地,二十年前被你们说成‘无主荒土’夺走。我儿子为此被打残,去年冬天冻死在桥洞。”她说完跪地痛哭,全场动容。
最终判决:刺史革职查办,流放交趾;同党十二人依罪论处;追回粮食两千四百余石,尽数返还受灾百姓。判决宣布之日,信都万人空巷,百姓自发焚香祭天,称“百年未见如此清明之政”。
此事震动朝野。原本对民议大会持观望态度的士人开始重新审视《宪章》价值。有儒生撰文道:“昔孔子欲行仁政而不得,今百姓自掌权柄反成治世,岂非天意?”也有老臣感叹:“吕哲当年所谋者,非改朝换代,乃是移风易俗。如今观之,确有成效。”
然而变革之路,终究不会平坦。
建安七年春,凉州突发兵变。原董卓旧部余党李?之侄李横,趁霍峻率军驻守河东之际,煽动部分不满“退役授田不足”的老兵作乱,占据武威,扣押使者,宣称“恢复汉室旧制,废除妖言惑众之《宪章》”。一时西北震动,商路断绝。
消息传至洛阳,朝廷哗然。有人主张立即派兵镇压,扬言“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诛之”;也有人担忧战火再起,百姓遭殃,建议遣使谈判。正当争论不休之时,蔡琰再次请命:“让我去武威。”
众人惊愕。一介女子深入叛军腹地,岂非送死?
她只答一句:“若言语尚能止戈,何必刀剑相见?”
遂单骑出关,仅带赵婴为副使,随行不过二十人,皆unarmed,手持《宪章》与医药。沿途百姓闻讯,纷纷加入护送队伍。至张掖,已有数百人相随;到酒泉,农夫送来干粮,牧民献上羊奶;进入武威境内,竟有上千平民手持火把,沿路照明,高呼:“莫伤蔡娘子!”
李横闻讯大惊,本欲射杀来使,却被部下拦住:“这些人不是军队,是我们的父老兄弟!你若动手,明日全城都会起来杀你!”
蔡琰入城那日,身穿粗麻布衣,头戴斗笠,怀中仍抱着那张焦尾琴。她在城中心广场设坛,不斥其罪,不谈政令,只当众弹奏一曲《关山月》。曲终,她起身说道:
“你们曾是边关将士,保家卫国,九死一生。如今退伍返乡,却无田可耕,无屋可居,心中愤懑,我能理解。但你们想过没有??你们抢回来的,真的是属于你们的东西吗?还是另一群穷人的活命口粮?”
台下寂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