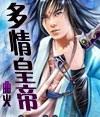沸腾文学>大召荣耀笔趣阁 > 第1005章 以忍换亡(第1页)
第1005章 以忍换亡(第1页)
邓金戈正要领命,盐铁使却跨出一步,抱拳谏道:“都督,眼下正值秋收,劳力本就紧缺,若再征丁壮,沿海盐场无人晒盐,今岁盐课……”
“盐课?”郑天锡冷哼道,“生死存亡之际,你连盐场都保不住,还谈什么课税?!”
他猛然拔出佩刀,“传令下去,盐场停工,榷场封市,市场所有丁壮编入水师,半月之内集结完毕,敢有拖延者,立斩不赦!”
话音落下,宝刀也已狠劈下去,堂案上立时木屑飞溅。刀锋嵌木,嗡嗡作响,包括那盐铁使在内,满堂噤声。
郑天锡环视众人,喘着粗气,好半晌才收刀回鞘,说道:“除了燕行之,项瞻还调来了两万镇安军,眼下就驻扎在泰山郡南境,距我平昌郡不过百里,可谓虎视眈眈。”
他重新坐下,沉声问道,“诸位有何对策?”
片刻沉默,堂下走出一青衫文士,拱手说道:“都督,某以为,项家军近日一切行动,皆意在朝廷,项瞻命燕行之断海,又调镇安军设防,无非是担心我青州趁机出兵。”
这文士姓高名巡,表字公卫,年有四十二三,早年便在郑天锡帐内执掌文书,后随他镇戍青州,被朝廷拟任都督府录世参军事,掌总录众曹文簿,勾检稽失,举弹善恶。
他为人刚正不阿,又腹有韬略,深得郑天锡喜爱和信任,被其引为心腹。
此时,郑天锡见他开口,焦躁情绪便也有所缓和,问道:“公卫想说什么,不妨直言。”
高巡浅浅一笑,又拱手道:“项瞻在南设防青州,在北围山阳郡而不攻,断粮道却不扰民,实为一石二鸟之计,其一,逼朝廷自乱阵脚;其二,刺激我青州防务,引都督先动。”
堂上一寂,郑天锡的呼吸都沉了几分:“继续说。”
高巡顿了顿,目光扫过堂内众人,接着说道:“朝廷失德,二王作乱,天下共知,项瞻以清君侧之名,只诛二王,不罪旁人,师出有名。”
他又看向堂上,“都督本已脱离朝廷,受百姓爱戴,如若此时出兵,一来有助纣为虐之嫌,二来正中项瞻下怀,他可是正愁没有对我军用兵的理由呢。”
郑天锡微微颔首,觉得在理,却又问道:“燕行之欺我太甚,我若执意动兵呢?”
高巡立即道:“都督若先动,项瞻便可昭告天下,青州郑氏私起甲兵,欲与二王合势窥阙,他便可起兵伐我,其兵多将广,粮道不扰而民心自附,我军却成众矢之的,海路被断,陆路被扼,盐铁皆无,坐困愁城,此所谓未战而先亡。”
“未战先亡……”郑天锡轻声呢喃,皱眉又问,“那,若我不动呢?”
“不动,项家军便安心困死山阳,待城中粮尽,二王或降或死,平保皇帝受缚,东召或亡,或名存实亡,项瞻彻底坐拥兖州,下一个目标……”高巡声音低缓,却字字如钉,“不是徐州,便是青州。”
郑天锡一怔,有些恍惚,他回味着高巡的话,好半晌,忽然轻笑一声:“若依着公卫所说,我青州不论动或不动,都免不了一个「亡」字?”
高巡却摇头:“亡字未必,却有一个「忍」字。”
郑天锡微微皱眉:“忍?”
“不错。”高巡说道,“忍到山阳郡易子而食,垒尸成山,民心厌乱,忍到项瞻不顾名声,强攻我青州,让天下人看明白,究竟谁,才是真正的操戈者。”
郑天锡仍是不解:“这又有何意义?”
“自然是有的。”高巡微微一笑,成竹在胸,“忍到项瞻师出无名,都督再举兵相抗,届时旗号便不再是「勤王」,也不是「清君侧」,而是「止兵戈、存百姓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