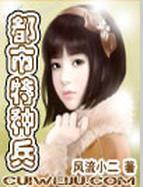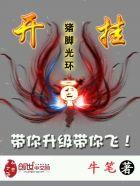沸腾文学>穿越重生1976年以前的 > 第686章 满室心意 孙辈们的孝与乐(第2页)
第686章 满室心意 孙辈们的孝与乐(第2页)
凌晨拎着行李,拉着何老师往自己住的西厢房走。门槛太高,他下意识扶了母亲一把,掌心触到她鬓角新添的白发,心里忽然软了一下。
“妈,给您这个。”他从包里摸出个厚厚的纸包,塞到何老师手里。二万元的分量压得她手腕微沉,她刚要开口,就听凌晨说:“大哥婚礼的开销,您拿着用。”
何老师把纸包往回推:“家里早备妥了,哪用得着这么多?你在香港打拼也不容易……”
“您放心花。”凌晨按住她的手,语气里带着点不容分说的笃定,“我现在是百万富翁了,这点钱不算啥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,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,可何老师的手却抖了起来。
纸包上还留着他的体温,她望着眼前的儿子——眉眼像极了他父亲,可那份沉稳干练,是自己缺席了多少年才长成的。想起他自小在外吃苦,想起他如今在香港创下的家业,想起他刚才说“百万富翁”时眼里的坦然,眼泪忽然就没了准头,顺着眼角往下淌。
“傻孩子……”她抬手抹了把脸,声音哽咽着,“妈不要你的钱,妈就盼着你好好的……”
凌晨把纸包塞进她口袋,又替她理了理衣襟:“我好得很,琳丫头和沫丫头也都好。您拿着钱,把大哥的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,就是给我最大的安心。”
窗外的红梅开得正盛,花瓣落进窗棂,带着点清冽的香。何老师攥着口袋里的纸包,忽然觉得那分量里,藏着的不只是钱,是儿子想把这些年亏欠的时光,一点点补回来的心意。她吸了吸鼻子,笑着推他:“快收拾行李去,等会儿外祖母该来催吃饭了。”
转身往外走时,她悄悄摸了摸口袋,纸包硌在掌心,像块暖玉。这个自出生就分开的小儿子,终究是凭着自己的本事,活成了她最骄傲的模样。
“凌晨,你外婆叫你呢!”沈晓雨的声音从月亮门边传来,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米糕。
凌晨应了声,转身就往二奶奶的正房小跑。刚跨进门槛,就见何家二奶奶正坐在太师椅上,手里捻着串檀木珠子,银簪子在花白的头发里闪着光。
“外婆。”他笑着递过手里的大袋子,“给您带了些粤剧录音带,都是红线女的新腔,还有您爱听的《帝女花》全本。”
二奶奶眼睛一亮,放下珠子接过袋子,指尖划过磁带盒上的戏装图案,嘴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:“还是你知道我心思,家里的旧带子都快听掉磁了。”
凌晨又掏出个油纸包,一打开,金黄酥脆的牛耳酥透着芝麻香:“这个是靖远老字号的,您尝尝,还热乎着呢。”
二奶奶捏起一块放进嘴里,咯嘣脆的声响里带着满足的笑:“你这孩子,打小就记着我爱吃这个。”她眯着眼看他,忽然拍了拍他的手,“在外头再忙,也得顾着自个儿身子,别学你外公,年轻时总熬着。”
廊下的风卷着梅香进来,混着牛耳酥的甜,粤剧磁带的油墨香,把祖孙俩的说话声裹得暖融融的。凌晨望着外婆鬓角的银簪,忽然觉得,这趟回来带的所有东西里,最珍贵的,莫过于此刻她眼里的笑意——像小时候,他偷偷把牛耳酥塞给她时,一模一样的温柔。
李校长掀着帘子进来时,手里还捏着个算盘,见二奶奶正乐呵呵地翻粤剧磁带,立刻凑上前笑道:“妈您看,还是您这外孙贴心,知道您的喜好。”说着朝刚进门的李修勇使了个眼色,“修勇也给您备了礼。”
李修勇赶紧从包里拎出个红木盒子,打开来,里面是根雕着龙头的拐杖,红漆亮得能照见人影:“外婆,这拐杖防滑,您平时在院里溜达着方便。”
二奶奶掂了掂拐杖,又摸了摸凌晨递来的磁带,嘴角的笑就没停过:“你们俩啊,一个懂我听戏的瘾,一个记着我腿脚的事,都有心。”她把拐杖往桌边一靠,龙头正好对着门槛,倒像个镇宅的物件。
李校长在一旁帮腔:“那是自然,您老的孙辈,哪能不贴心?”说着给凌晨使了个眼色,眼里的得意藏不住——这俩孩子,一个文气懂暖,一个实在知孝,倒把老太太哄得眉开眼笑。
二奶奶捻着牛耳酥,忽然朝李校长瞥了眼:“还是凌晨这粤剧带对味,比你去年给我买的戏文册子强,能听能看的。”李校长嘿嘿笑着挠挠头,倒也不恼——在这老太太面前,晚辈们争着尽孝,本就是件乐事。
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,落在龙头拐杖的红漆上,落在磁带盒的戏装上,也落在祖孙几代人含笑的脸上。这热闹里没有虚礼,只有实打实的惦记,像桌上的牛耳酥,脆生生的,甜到心里头。